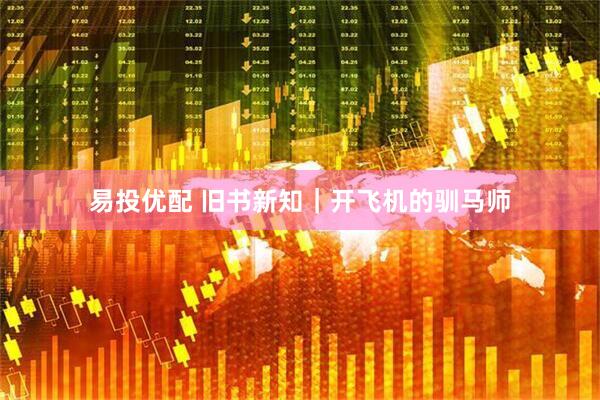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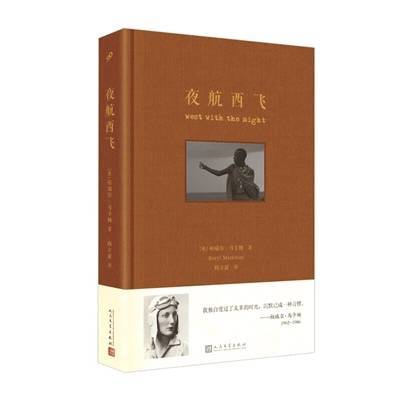

海明威在写给传奇编辑马克斯威·帕金斯的信中问他:“你读过柏瑞尔·马卡姆《夜航西飞》了吗……她写得很好,精彩至极,让我愧为作家。”
然而柏瑞尔·马卡姆并不是专业作家,而是专业的赛马训练师、飞行员,她也是第一位完成从东到西横越北大西洋单机飞行的人。
她出生于1902年,四岁时跟随父亲来到非洲,从此与非洲结下不解之缘,直到1986年在肯尼亚离世。她的一生像是扎根并融化在非洲肥沃的土地里,又始终穿梭于这片土地上方的云层中。这本《夜航西飞》是她关于非洲的回忆。她用散文的方式描述自己眼里的非洲,给我们讲述她在当地的朋友:他们的模样、性情和勇气,还有自己如何同他们一起挥舞着长矛打猎。
她告诉我们自己如何与马相处、如何驯马并赢得比赛。当然,还有关于她飞行的故事,在书中,柏瑞尔·马卡姆大段大段地描写独自飞行的感受,并完整地回忆了自己飞越北大西洋的过程。
我想用壮美来形容她的文字和她的故事,这本书完全配得上这个词。这本书虽然是关于她的故事,但读者几乎感觉不到她是“主角”——我们仿佛看不到她,而是“带上”她的眼睛,“穿上”她的手,“踩进”她的脚,甚至“钻进”她的灵魂,全然地进入她所经历的时空。
她对自己好像没什么兴趣。我感觉只在她写驯马的段落中,透过马的眼睛看到过她,那个被摔下马背、头发如同稻草般的倔强的姑娘。
在文字间,这样“无我”的态度并没有世故的痕迹,那不是大家闺秀款款低眉的教养,而是充满生命张力的向外的好奇心。
不仅是对自己,柏瑞尔·马卡姆对所有经历的人和事都鲜有判断和评价,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起所观所感。她也从未在书中惊乍,即便是讲述自己和狮子对战、围猎疣猪和大象、徒手打死狒狒这些惊心动魄的经历,也带着几分新闻简报般的平静,甚至还有幽默。有时我会感觉她有一种旁观的冷漠,然而很快又发现自己从未在文字中体验过如此这般巨大的热情。
她笔下的非洲也如同文字般壮美。那种对这片土地的敬畏自然地流淌出来,却没有唯唯诺诺的卑微。就像书中写到,当她起飞升空,飞机便是她的星球,而地球则是“另一颗遥远的星星”。
我会在她的文字中体验到孤独,尤其是她不止一次写到独自一人夜航的感受。但这些孤独里没有绝望和自怨自艾,也没有任何胁迫或拒绝,而更像是在描述某种冷饮,让人想尝尝,或者不尝也行。
她写马时稍有不同,她对马的情感细腻,情绪也要充沛很多,在《我将带给你好运》一章,她洋溢地写下了自己训练的马参加比赛的过程,让人不禁跟她一起揪着心提着胆,非常精彩。也只有在这样细腻的瞬间,可能才会有机会意识到这位彪悍不羁的作者,是一位情感细腻的女性。在这本关于她的书中,很少见到性别标识,她毫不在意自己的性别——就像本就应该的那样。她从未明讽暗刺男女不公或表达平权诉求,甚至没有想要暗示: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在男性更加擅长的领域,达成了许多他们都无法企及的成就的事实,她似乎也从未因此骄傲。如果她有过一丝骄傲,那也只是因为事情,而不是因为身份。
另一方面,她也没有想要通过淡化性别带来的差异来跳出桎梏,她如常地面对自己的细腻和柔弱,就好像面对自己的头发和眼睛一般。
这就如同她写到自己的许多经历时那样,她可能认为性别这件事情“不值一提”。
这本书值得放在手边,一读再读,对我来说,它更像是忙碌世俗生活的一个暂停键。就像它的译者陶立夏在译后记中说的那样:这本书或许只是短暂的逃离,让你去往一个不复存在的非洲。合上书的时候,什么都没有改变。但你知道,曾有过那样的生活、那样的世界、那样的信念、那样的人。
文/邱岳
编辑/周超
万隆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